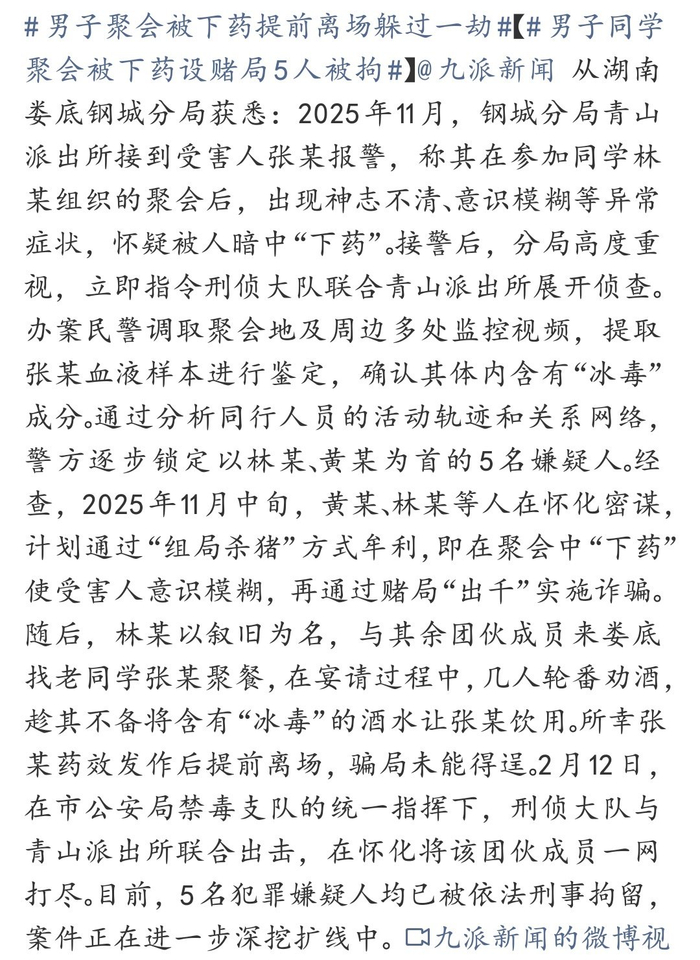这几个迹象,表明孩子内心很缺爱
我当了十五年父亲,直到那个秋天的家长会,才第一次尝到为人父的苦涩。
教室里的风扇吱呀作响,班主任念作文的声音平缓得让人心慌。
当她念到儿子那篇《我的爸爸》时,我下意识攥紧了手里的钥匙串。
“我的爸爸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每天七点零五分准时进门,会按顺序问三个问题:作业写完了吗?考试第几名?今天听课都懂了吗?”
钥匙串硌得手心发疼。
我能感觉到周围家长投来的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庆幸,更多的是感同身受的无奈。
“他给我买最新款的球鞋,却从没看过我打球。有时候我想,他爱的到底是能考满分的我,还是真实的我?”
我低下头,第一次在儿子的事情上感到无地自容。
一、沉默的轰鸣
家长会结束后,我在学校对面的便利店坐了整整两个小时。
玻璃窗上雨水蜿蜒而下,像极了我此刻支离破碎的心情。
回到家时已经九点多。
儿子房间的门缝下透出微弱的光,我站在门口,手抬起又放下。
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最终还是没有敲下去。
第二天清晨,我破天荒地在周末六点就醒了。
厨房里,我笨拙地照着手机菜谱做葱油拌面,却把葱段炸得焦黑。
儿子起床看见餐桌上的面,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我去图书馆了。”他吃完最后一口面,背起书包。
“我送你。”我抓起车钥匙,语气急切得像个想要表现的孩子。
车里的二十分钟,我们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等红灯时,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他,发现他居然已经这么高了,座位都要调到最靠后。
上次认真看他是什么时候?好像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
二、细节里的求救信号
从那天起,我开始学着用新的方式观察儿子。
他书桌上那个陶瓷笔筒,每次大考前都会被无意识地转来转去,边缘已经磨得发亮。
他说“无所谓”时,右手总会不自觉地捏紧衣角。
篮球赛输掉后,他会一个人在球场待到天黑,背影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单薄。
最让我难受的,是有次帮他整理书桌时,看见草稿纸上一行用力写下的字。
“如果我不是第一名,还会有人爱我吗?”
字迹深深陷进纸里,像是要把这句话刻进心里。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抽了半包烟。
想起他六岁时,举着满分试卷冲我笑的样子,两颗门牙刚掉,说话漏风却格外开心。
原来从一开始,我就给了他错误的暗示——只有优秀才配得到爱。
三、笨拙的转身
改变是从问话的方式开始的。
我把“作业写完了吗”换成“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
把“考试第几名”换成“最近是不是很累”。
起初他总是用“就那样”“还行”敷衍我。
但我能感觉到,他紧绷的肩膀在慢慢放松。
十一月的一个雨夜,他数学考了六十八分,进门就躲进房间。
我热了杯牛奶,敲门进去时他正对着试卷发呆,眼眶发红。
“我高一的时候数学考过三十八分。”我把牛奶放在桌上,热气在灯光下袅袅升起。
他猛地抬头,眼睛瞪得很大,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真的,”我在他床边坐下,床板发出吱呀一声,“后来我每天放学后多做三道题,期末就及格了。”
他轻轻“嗯”了一声,低头喝了一口牛奶。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来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展示软弱的真实的人。
四、门里的光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期末考试前。
学校演讲比赛的前一晚,我听见他在房间里练习。
透过门缝,我看见他对着镜子一遍遍调整手势,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珠。
“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爸爸。不是因为他给了我多好的生活条件,而是因为他终于看见了我。”
“当他第一次问我‘今天开不开心’时,我就知道,那扇我以为早已关死的门,其实一直虚掩着。”
我站在门外,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地板上留下深色的印记。
比赛那天,我请了假坐在第一排。
当他说到“虚掩的门”时,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
他朝我眨眨眼,那个调皮的表情,让我恍惚间又看到了他五岁时的模样。
五、看见的艺术
如今儿子已经上高二了。
我们还是会为成绩吵架,为玩游戏的时间讨价还价。
但不同的是,我们学会了在争吵后一起下楼吃烧烤,在僵持时给对方发台阶式的微信。
上周整理书房,他翻出小时候的相册,指着一张照片笑:“爸,你看你抱我的样子,像捧着一个易碎品。”
照片上,我确实僵硬得像个第一次抱娃娃的青少年。
“现在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揉揉他的头发,发丝比想象中柔软,“还在学。”
他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这时我才恍然,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学习如何做一个“成功”的父亲,却忘了最重要的是先做一个真实的、会脆弱的父亲。
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扇门,它从未上锁,只等一双愿意停留的手。
如果你也觉得和孩子之间隔着一道门,不妨试着换一种敲门的方式——不是用期望的力度,而是用理解的温度。
因为真正的门从来不在孩子心里,而在我们看待孩子的眼睛里。
发布于:浙江
https://k.sina.cn/article_6574896440_187e4f53800101ctu4.html